李陀批评家
1978年,39岁的“产业工人”李陀正在贵阳修改关于李四光的剧本,电话传来,他的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李陀从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重型机械厂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成了一名“驻会作家”。 驻会作家”李陀看了很多外国作品后,开始觉得自己这么写作不行,1982年他决定暂时放下小说,先做积累,结果“小说就一直放下,最后就变成搞文学批评的了”。1986年,“文学批评家”李陀又调到《北京文学》当副主编,跟主编林斤澜搭档,推出了很多先锋小说,如:马原、苏童、莫言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1989年6月2日,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访问学者李陀前往美国。一访就是5年,1994年李陀才第一次回国,此后他又陆续在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大学当访问学者,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直到现在。1980年代,至少都认真,能争吵1980年代,各个编辑部还都把“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作编辑的天职。当时文学的繁荣局面,得益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而且编辑大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那种文学理想,跟“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期刊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编辑一旦发现好作品,就会把作者请来,住下改稿,成熟了就发表。发表后还会请作者来开会。其他刊物的编辑看到新作者的出现,也都会马上约稿。编辑部内部气氛也很活跃。一篇文章来了,年老的说不能发,年轻的说一定得发。类似冲突是各个编辑部的常态。1980年代的批评也是有权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约下的批评家(以下简称为“官方批评家”),也是有权威性的。“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不少官方批评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批评家了。不像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懂行。再者,相当一部分官方批评家人品很好。比如夏衍就具有某种人格魅力,对他的权威,作家有所反
驻会作家”李陀看了很多外国作品后,开始觉得自己这么写作不行,1982年他决定暂时放下小说,先做积累,结果“小说就一直放下,最后就变成搞文学批评的了”。1986年,“文学批评家”李陀又调到《北京文学》当副主编,跟主编林斤澜搭档,推出了很多先锋小说,如:马原、苏童、莫言和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1989年6月2日,应芝加哥大学之邀,访问学者李陀前往美国。一访就是5年,1994年李陀才第一次回国,此后他又陆续在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大学当访问学者,教中国现当代文学,直到现在。1980年代,至少都认真,能争吵1980年代,各个编辑部还都把“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作编辑的天职。当时文学的繁荣局面,得益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而且编辑大都是有文学理想的人,那种文学理想,跟“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期刊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当时编辑一旦发现好作品,就会把作者请来,住下改稿,成熟了就发表。发表后还会请作者来开会。其他刊物的编辑看到新作者的出现,也都会马上约稿。编辑部内部气氛也很活跃。一篇文章来了,年老的说不能发,年轻的说一定得发。类似冲突是各个编辑部的常态。1980年代的批评也是有权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约下的批评家(以下简称为“官方批评家”),也是有权威性的。“伤痕文学”,就是在官方批评家的提倡、鼓励、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不少官方批评家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是批评家了。不像现在,很多官员都不懂行。再者,相当一部分官方批评家人品很好。比如夏衍就具有某种人格魅力,对他的权威,作家有所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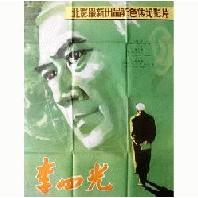 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1985年以后形成的新批评家群体,他们的权威性来自文学发展的创新诉求。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上,官方批评家总是顾虑重重。而新批评家想的就是文学本身。可以说,“纯文学”潮流并不是作家创造的,而是新批评家创造的,至少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创造的。当时的情况,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评家则把大旗树起来。1980年代初,官方批评家,如冯牧、雷达都是伤痕文学的支持者、宣传者,可我们都很怀疑,觉得伤痕文学不是我们期待的文学。然而我们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后,何立伟、阿城陆续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们没有构成潮流。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们看成“寻根文学”的先头部队。等到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面世,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也正是这些作品,造成了当时批评界最严重的分化。如何看待虚构的历史?如何看待跟社会主义革命无关的小说?官方批评家有点乱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丧失了批评能力。这时候,年轻一代批评家站出来了。比如季红真,对阿城作品的诠释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今天看来,那种诠释很成问题,但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她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年轻批评家,像吴亮、蔡翔、程德培,黄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广泛认同,堪称一夜成名。1987年,余华、苏童、北村、格非、孙甘露、残雪这批作家出来了。但包括新潮批评家在内,大家都没注意。批评界还有人说1987年前后没有好作品,“文学陷入了低谷”。新潮批评群体的成员,一般来说,跟作协、文联系统的关系都很疏远。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来是工人,写了很好的批评文章之后,被调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在编《上海文学》理论版时,他仍然坚持撰写独立的批评文章。当然,新潮批评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协会员,但一开始都不是。当时发表批评文章的文学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报》、《钟山》、《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
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1985年以后形成的新批评家群体,他们的权威性来自文学发展的创新诉求。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的问题上,官方批评家总是顾虑重重。而新批评家想的就是文学本身。可以说,“纯文学”潮流并不是作家创造的,而是新批评家创造的,至少是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创造的。当时的情况,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评家则把大旗树起来。1980年代初,官方批评家,如冯牧、雷达都是伤痕文学的支持者、宣传者,可我们都很怀疑,觉得伤痕文学不是我们期待的文学。然而我们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后,何立伟、阿城陆续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们没有构成潮流。从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们看成“寻根文学”的先头部队。等到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面世,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也正是这些作品,造成了当时批评界最严重的分化。如何看待虚构的历史?如何看待跟社会主义革命无关的小说?官方批评家有点乱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丧失了批评能力。这时候,年轻一代批评家站出来了。比如季红真,对阿城作品的诠释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今天看来,那种诠释很成问题,但当时震动很大,因为她根本不提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家都觉得非常新鲜。年轻批评家,像吴亮、蔡翔、程德培,黄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广泛认同,堪称一夜成名。1987年,余华、苏童、北村、格非、孙甘露、残雪这批作家出来了。但包括新潮批评家在内,大家都没注意。批评界还有人说1987年前后没有好作品,“文学陷入了低谷”。新潮批评群体的成员,一般来说,跟作协、文联系统的关系都很疏远。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来是工人,写了很好的批评文章之后,被调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在编《上海文学》理论版时,他仍然坚持撰写独立的批评文章。当然,新潮批评群体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协会员,但一开始都不是。当时发表批评文章的文学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报》、《钟山》、《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 1980年代,由于精神生活长期匮乏,所以全民都热爱文学。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关于文学批评的,也会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崛起》,发在一个“很偏远”的杂志上,但当时很轰动,官方批评家都围剿他。全世界都一样,作家一般都假装不在乎批评。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说,文学批评只不过是长在文学这棵树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评;不但看,批评还能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990年代,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1990年代,新潮批评家群体很快就消失了。年轻的职业批评家,要么到学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别的。进入大学的那部分批评家,成了学术机制里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应该面对普通读者,学术研究应该面向学术界,完全是两回事。张颐武等学者,习惯于把学术名词搬到报纸上,搞得谁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却觉得很深奥。1990年代初,此风盛极一时。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实现“市场化”的群体,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与出版、销售合成一体,很快就被“收编”进了商家宣传这个炒作体制当中。商业大潮中,期刊也没法不“湿鞋”。大概只有《读书》至今还没有拿钱买版面的事情。1990年代,记者、编辑中诞生了一个很大的批评群体,这个群体也很快就与商业机制融为一体了。那种批评无所谓方法,没任何节制,毫无标准地吹捧作品。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对文学创作起着关注、监督、反省作用的批评家队伍就不复存在了。1990年代以后,“70后”、“80后”、“个人写作”,看似火爆。不过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些批评家滥用命名权而已。滥用命名权,也是1990年代以后批评家权威性丧失的一个注解。所以,在1990年代,文学批评没什么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作为文学批评家,李陀算得上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不少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他提出的“小人时代的文学”在网上招致骂声一片,他仍然告诉记者,至今还是有着同样的观点。他说,他很欢迎大家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和他进行讨论,只要提出了问题,就能够通过探讨取得收获。李陀在《读书》上号召广大作家,为工农写作,替群众代言。他说:“那些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感情、思考、喜怒哀乐、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怎么来表达?”他认为,如今的文学可以称作“小人时代的文学”,特征之一是“文学的内容越来越琐碎”,很少有作家再去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和需求。针对网上不少人支持的“小人时代的文学正说明了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人需要代言,是一种文学的进步”这种观点,李陀认为,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最底层的人的需求。“他们说,网络发达了,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倒要问问,那些没钱买电脑的人呢?那些没钱上网吧的人呢?人们怎么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李陀坚持认为,作家不能太过“小资”,要有社会责任感。或许,这就是他长期坚持的“知识分子要用‘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的表现吧。不久前,李陀的台湾同行南方朔告诉记者,写评论是他的谋生手段而非兴趣所在。记者把这个问题抛在李陀面前的时候,李陀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他说,自己不是个聪明人,不可能同时做很多事情——“今后,我就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搞文学批评。”
1980年代,由于精神生活长期匮乏,所以全民都热爱文学。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关于文学批评的,也会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崛起》,发在一个“很偏远”的杂志上,但当时很轰动,官方批评家都围剿他。全世界都一样,作家一般都假装不在乎批评。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说,文学批评只不过是长在文学这棵树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评;不但看,批评还能对他们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990年代,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1990年代,新潮批评家群体很快就消失了。年轻的职业批评家,要么到学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别的。进入大学的那部分批评家,成了学术机制里的一部分。文学批评应该面对普通读者,学术研究应该面向学术界,完全是两回事。张颐武等学者,习惯于把学术名词搬到报纸上,搞得谁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却觉得很深奥。1990年代初,此风盛极一时。文学批评领域率先实现“市场化”的群体,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与出版、销售合成一体,很快就被“收编”进了商家宣传这个炒作体制当中。商业大潮中,期刊也没法不“湿鞋”。大概只有《读书》至今还没有拿钱买版面的事情。1990年代,记者、编辑中诞生了一个很大的批评群体,这个群体也很快就与商业机制融为一体了。那种批评无所谓方法,没任何节制,毫无标准地吹捧作品。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对文学创作起着关注、监督、反省作用的批评家队伍就不复存在了。1990年代以后,“70后”、“80后”、“个人写作”,看似火爆。不过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一些批评家滥用命名权而已。滥用命名权,也是1990年代以后批评家权威性丧失的一个注解。所以,在1990年代,文学批评没什么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销。作为文学批评家,李陀算得上成就斐然,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不少的质疑和反对的声音。对于这一点,他并没有太过激烈的反应。他提出的“小人时代的文学”在网上招致骂声一片,他仍然告诉记者,至今还是有着同样的观点。他说,他很欢迎大家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和他进行讨论,只要提出了问题,就能够通过探讨取得收获。李陀在《读书》上号召广大作家,为工农写作,替群众代言。他说:“那些没有笔杆子的下岗工人、民工、还在穷困中挣扎的农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感情、思考、喜怒哀乐、他们的‘显意识’和‘潜意识’,怎么来表达?”他认为,如今的文学可以称作“小人时代的文学”,特征之一是“文学的内容越来越琐碎”,很少有作家再去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和需求。针对网上不少人支持的“小人时代的文学正说明了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人需要代言,是一种文学的进步”这种观点,李陀认为,持这种意见的人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而没有考虑到真正的最底层的人的需求。“他们说,网络发达了,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倒要问问,那些没钱买电脑的人呢?那些没钱上网吧的人呢?人们怎么倾听得到他们的声音?”李陀坚持认为,作家不能太过“小资”,要有社会责任感。或许,这就是他长期坚持的“知识分子要用‘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这种观点的表现吧。不久前,李陀的台湾同行南方朔告诉记者,写评论是他的谋生手段而非兴趣所在。记者把这个问题抛在李陀面前的时候,李陀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他说,自己不是个聪明人,不可能同时做很多事情——“今后,我就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搞文学批评。”
更多李陀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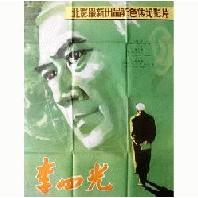 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
抗,但也乐于服从。第三,他们的权威建立在一个共识之上:“文革”后应该有个新局面。在打破文化专制主义这点上,官方批评家、非官方批评家、作家又是一致的。最典型的是冯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国作协的领导,又是有见地的文学批评家。有时他要拿出官员身份,进行政策实施;而作为批评家,他又要维护好的作品,鼓励文学思潮。这两个身份的内在冲突,让他左右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