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芭娜娜创作特点
 对日常性死亡事件的现代性书写是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真实的日常性死亡主题在她的笔下反复出现,形成了吉本小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死亡”是吉本切入现实、品评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她契入故事的缘起。在她的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她的这个“独特视角”在审视故事的进展。例如在《厨房》中,“祖母死了”,平淡的一句话引出一段孤独、曲折的城市故事,由此樱井失去了所有的血亲,失去了安身之所,走人了一个无任何血缘关系、陌生的家庭。吉本在死亡这个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的表达上,没有安排气势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没有战争这个特殊场景的设定,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没有重于泰山的不平凡的事迹,她把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放在一个更为司空惯见,更为平凡的环境之中。一次感情的波动或失败,一场疾病,一段热烈的情恋,甚至一次误会,一个疏忽都可能造成死亡。为爱情而死,因苦闷自杀,因偶然的失误造成车祸而死,不明缘由的人间蒸发,自然的生老病死一他们的死没有崇高的意义,也没有深刻的阶级、历史、文化原因。可以说,死亡是吉本艺术地把握文学世界、塑造人物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在死亡场景的设定、渲染上,吉本也自有她独特的表现方式,或浅豁或深刻,或淡远或执著。幽幽的哀感与朦胧的暗示,有分离、永别、不忍弃绝之意,这样就在读者的心灵投入一缕悲思,顺着这一缕悲思的引领,身不由己地赋予人物命运以真诚的同情,一起悲愤,一起感伤。从而达到渲染主题、烘托故事高潮的效果。故事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孤独的小人物,然而,作者总是满怀爱意地关注他们,尽管她笔下的人物没有高大形象,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令人羡慕的固定职业,甚至没有家庭。吉本的长处在于描写这些平凡有趣的人物,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并不可避免地遭遇死亡、凝视死亡,到最后超越死亡的几个痛苦、难熬的“死亡”磨砺过程,在孤独、艰难、平凡的生活中一步步地走出死亡的阴影,最终走向求“生”之路。无论经受多少磨难,吉本笔下的那些飘荡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的弱小、彷徨的孤影们终会战胜苦难,逐渐变得成熟。作者以独特的感性描述出现代城市人的孤独感及游走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之间的人生体验。
对日常性死亡事件的现代性书写是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真实的日常性死亡主题在她的笔下反复出现,形成了吉本小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死亡”是吉本切入现实、品评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她契入故事的缘起。在她的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她的这个“独特视角”在审视故事的进展。例如在《厨房》中,“祖母死了”,平淡的一句话引出一段孤独、曲折的城市故事,由此樱井失去了所有的血亲,失去了安身之所,走人了一个无任何血缘关系、陌生的家庭。吉本在死亡这个亘古不变的文学主题的表达上,没有安排气势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没有战争这个特殊场景的设定,作品中的人物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没有重于泰山的不平凡的事迹,她把人生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放在一个更为司空惯见,更为平凡的环境之中。一次感情的波动或失败,一场疾病,一段热烈的情恋,甚至一次误会,一个疏忽都可能造成死亡。为爱情而死,因苦闷自杀,因偶然的失误造成车祸而死,不明缘由的人间蒸发,自然的生老病死一他们的死没有崇高的意义,也没有深刻的阶级、历史、文化原因。可以说,死亡是吉本艺术地把握文学世界、塑造人物的一种独特方式。而在死亡场景的设定、渲染上,吉本也自有她独特的表现方式,或浅豁或深刻,或淡远或执著。幽幽的哀感与朦胧的暗示,有分离、永别、不忍弃绝之意,这样就在读者的心灵投入一缕悲思,顺着这一缕悲思的引领,身不由己地赋予人物命运以真诚的同情,一起悲愤,一起感伤。从而达到渲染主题、烘托故事高潮的效果。故事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平凡、孤独的小人物,然而,作者总是满怀爱意地关注他们,尽管她笔下的人物没有高大形象,没有远大的理想,没有令人羡慕的固定职业,甚至没有家庭。吉本的长处在于描写这些平凡有趣的人物,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家庭变故,并不可避免地遭遇死亡、凝视死亡,到最后超越死亡的几个痛苦、难熬的“死亡”磨砺过程,在孤独、艰难、平凡的生活中一步步地走出死亡的阴影,最终走向求“生”之路。无论经受多少磨难,吉本笔下的那些飘荡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间的弱小、彷徨的孤影们终会战胜苦难,逐渐变得成熟。作者以独特的感性描述出现代城市人的孤独感及游走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之间的人生体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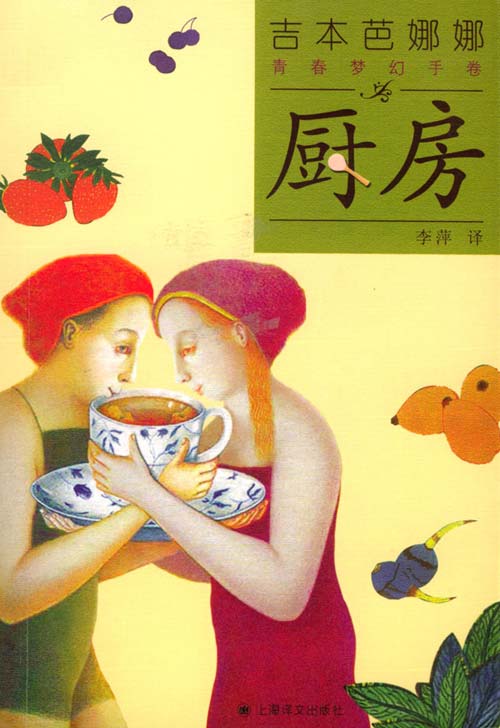 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与死的非对立性。死蕴含着生,生也包含着死。死是人生的极限,个体的毁灭,死的份量是无法估量的,它留给读者的应该是无尽的痛苦。然而,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是,吉本小说中的死亡留给读者的往往不是悲哀、沉重的感受,而是通过死亡事件描写处于极限中的人际关系,无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中产生的类似家族成员般的温情表现;通过“死”的体验,建构一种深层次的真实的人性关怀;通过“死亡”这一极限的设定,达到一种丧失语言的极限状态,从而与死相关联的主人公们,在处于极限、经历苦难的心路历程之后,感觉、视觉变得多层次化,从而进一步打破惯常的价值观,体味丰富的感性,建构起新的心理价值。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中充满了孤独和寂寞,但小说中没有所谓的恶人,这反映出日本年轻人希望生活在充满诚实和善良的美好世界的愿望。读者沉浸在吉本芭娜娜设定的这个世界中,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可以放下现实的重负,在这种孤独、却是纯净的世界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共鸣,得到休憩。这是吉本芭娜娜文学的“疗伤”功能,同时,也是文学欺骗性的一种表现。这些主人公都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东西,已经无法找到生命的价值,他们已经不相信靠自己的某些积极的人生态度或者行为能够获得理想中的结果,只是按照“一时的想法”生活,靠“感觉”行动。而主人公能够凭借“感觉”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恰恰表现出孤独中所产生的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理解和共鸣。丧失了的东西、空虚的心境成为将男女主人公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他们共同分担孤独和寂寞,寻求相互间的理解和共鸣,并以此相互填补心灵的空洞,获得安慰。这是吉本芭娜娜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通俗性吉本芭娜娜没有走日本正统文学的道路,而是更加重视大众化的较“低”层次,在小说中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和文学修饰,基本上是用词比较简单的口语文体,而且具有较强的叙事性,渲染出透明的感性和主人公—“我”面向读者娓娓诉说的亲近气氛。小说中大量使用渲染临场气氛的对话,加之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年轻读者的心声,很容易使读者接受其中的故事和情节,并产生近似亲身体验的感觉,满足了读者希望有人与自己促膝谈心、打破自己孤寂情绪的潜在的精神需求。这也是吉本芭娜娜的小说被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在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孤独和现代社会的冷漠以及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抗拒心理。芭娜娜认为只要是人就必定会有相通之处,因此,在创作中她并没有刻意地思考所谓主流的东西,而是反复琢磨如何通过展现人之共性,触发心灵的共鸣去赢得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她所理解的文学并非经邦济国的大业,而是“一个人在回家途中随意走进书店,‘啊,这是新刊。’于是买上一册。回家后在阅读的两三个小时、或者两三天时间里,心境略有改变,或是在人生中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时能倏然想起那本书的内容并由此获得慰籍。”这就是芭娜娜的文学理想,是吉本隆明所说的“不同的小说概念”,也是芭娜娜取舍文学素材的依据和标准。为此,她选择了普遍性,摒弃了特殊性,她描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排除了历史人物的叱咤风云或耀眼明星的妮紫嫣红。她曾说自己全部的兴趣就在于普通的事物:“在平凡得无法区别的一天,一如既往地来到街上,普通的人们在做些什么”。芭娜娜的这种文学观直接带来了她作品的一大特色—“通俗性”。她本人对“通俗性”的解释是:普通的人能够阅读并理解。为此她在写作时尽量避免出现阻滞读者思维的情况,她希望即使是与书无缘的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也能够顺畅无阻。芭娜娜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把自己置换为一个读者,她总在不停地揣摩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获得些什么,同时想象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这与村上春树“尽可能让作者与读者处于并列位置”的原则不谋而合。芭娜娜创作时的价值判断来源于读者的好恶,而非专家学者的评论,或编辑人员的意向、文坛同人的希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本隆明说她是“读者专家”。芭娜娜为实现通俗性而采取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渲染情绪。情绪是时间、地点、情节、人物、环境等小说诸要素当中最不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之一,却是芭娜娜最为重视的一项。她认为,“世界各国的人能够共同理解的东西不是语言,而是类似于情绪的东西”,比如“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了这样的事有了这样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走过这样的地方于是情况变成了这样等等”。因此,她总是着意去捕捉人在某个特定瞬间的极其微妙的心理感觉。她的作品往往于不经意间、在读者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触动他们内心深处最为脆弱和柔软的部分。当然并非通篇都遍布着与读者情绪的接合点,不同的读者总是对不同作品的不同细节有着特殊的感触,在阅读进行到某一特殊位置时才能感受那种因共振而形成的心灵冲击、体味因理解而带来的悲喜交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芭娜娜认为小说是“一对一”的艺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是“一对一”的关系,小说营造的情绪渗透于读者内心,读者也由此深入到作品内部。芭娜娜文学的通俗性还反映在叙述语言上。她的作品中,第一主角几乎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女性,同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仿佛是女主人公在向读者娓娓倾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语言风格简洁平实,带有显著的口语体色彩。日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非常大,书面语整伤、规范、明确,口语简短、随意、暖昧。芭娜娜作品中频繁出现大段的人物对话,此外还有大量的心理独白。这部分语言几乎没有经过文学的润色和修饰,如果诉诸声音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录音片段。其中还包含了许多日本现代生活中、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使用的理语、流行词汇以及刚刚出现的外来语,等等。即使是叙述语言也都简单明了,以短句居多,没有日语正式文体中常见的那种烦琐冗长的敬语,从而摆脱了敬语所特有的生硬疏远的感觉,因此非常接近生活的原样。另外,芭娜娜多使用浅显易懂的假名词汇,而极少那些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所喜用的艰深的汉字词汇。就连数字也大都是阿拉伯数字而不是汉字。日语是竖行排列,一旦出现阿拉伯数字就不得不改变阅读方向,所以一般来讲都采用汉字表示。但芭娜娜却乐于使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一目了然的阿拉伯数字。综观全篇,汉字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假名在纸面上占用空间较之汉字要大上几倍,一个汉字通常可以对应数个假名,而大量存在的对话又需要不断换行,所以也有一些持否定意见的评论者批评芭娜娜的作品是“注水小说”,缺乏内容,借助分段留白等手段来拉长篇幅。尽管芭娜娜的文学语言本身非常朴素,然而营造出来的氛围却细腻玄妙,极富感性,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超现实吉本芭娜娜的很多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只是简短的话语连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或是与人谈天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有种自然亲切的感觉使得读者的情绪随着她悠缓的语气而起伏。小说中简单的模式中追诉往事这一倒序方式,像是再跟读者对话,以开始的结局引起读者的想象,为探清缘由而有接着看下去的欲望,又起到了拉开读者与文本距离的作用,适时地提醒作者这是别人的故事。除了倒叙这一手法,超现实描写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小说的主人公沉陷在无边的黑暗中时,超现实现象总是以梦境或超能力者显现能力的形式进入她的生活,从而形成了亦真亦幻、真真假假、神秘无解的艺术境界。吉本小说的巨大感染力量是她的感性的描写显现的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悲剧力量。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无限制地使读者哀伤下去,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读者认清现状从黑暗中走出来,让读者振奋起来,努力改造人生。吉本芭娜娜为了达到她期望的效果,巧妙地植入了超现实的描写,帮助读者从哀伤的故事中摆脱出来,仿佛芭娜娜在强化一种生活观念,是运用艺术描写的方式在强化。芭娜娜在小说中添加超现实元素,造成了一定的间离的效果,让读者沉浸于小说人物的悲伤忧愁之中的同时,可以适时地审视自我、调节自我,不忘领会吉本芭娜娜这样写的目的和意义—调整自我从悲伤中走出来,回归现实,正视现实。
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与死的非对立性。死蕴含着生,生也包含着死。死是人生的极限,个体的毁灭,死的份量是无法估量的,它留给读者的应该是无尽的痛苦。然而,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是,吉本小说中的死亡留给读者的往往不是悲哀、沉重的感受,而是通过死亡事件描写处于极限中的人际关系,无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中产生的类似家族成员般的温情表现;通过“死”的体验,建构一种深层次的真实的人性关怀;通过“死亡”这一极限的设定,达到一种丧失语言的极限状态,从而与死相关联的主人公们,在处于极限、经历苦难的心路历程之后,感觉、视觉变得多层次化,从而进一步打破惯常的价值观,体味丰富的感性,建构起新的心理价值。吉本芭娜娜的文学世界中充满了孤独和寂寞,但小说中没有所谓的恶人,这反映出日本年轻人希望生活在充满诚实和善良的美好世界的愿望。读者沉浸在吉本芭娜娜设定的这个世界中,虽然是暂时性的,但可以放下现实的重负,在这种孤独、却是纯净的世界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共鸣,得到休憩。这是吉本芭娜娜文学的“疗伤”功能,同时,也是文学欺骗性的一种表现。这些主人公都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东西,已经无法找到生命的价值,他们已经不相信靠自己的某些积极的人生态度或者行为能够获得理想中的结果,只是按照“一时的想法”生活,靠“感觉”行动。而主人公能够凭借“感觉”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恰恰表现出孤独中所产生的发自内心的真正的理解和共鸣。丧失了的东西、空虚的心境成为将男女主人公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他们共同分担孤独和寂寞,寻求相互间的理解和共鸣,并以此相互填补心灵的空洞,获得安慰。这是吉本芭娜娜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通俗性吉本芭娜娜没有走日本正统文学的道路,而是更加重视大众化的较“低”层次,在小说中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和文学修饰,基本上是用词比较简单的口语文体,而且具有较强的叙事性,渲染出透明的感性和主人公—“我”面向读者娓娓诉说的亲近气氛。小说中大量使用渲染临场气氛的对话,加之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年轻读者的心声,很容易使读者接受其中的故事和情节,并产生近似亲身体验的感觉,满足了读者希望有人与自己促膝谈心、打破自己孤寂情绪的潜在的精神需求。这也是吉本芭娜娜的小说被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在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年轻一代的内心孤独和现代社会的冷漠以及他们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抗拒心理。芭娜娜认为只要是人就必定会有相通之处,因此,在创作中她并没有刻意地思考所谓主流的东西,而是反复琢磨如何通过展现人之共性,触发心灵的共鸣去赢得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她所理解的文学并非经邦济国的大业,而是“一个人在回家途中随意走进书店,‘啊,这是新刊。’于是买上一册。回家后在阅读的两三个小时、或者两三天时间里,心境略有改变,或是在人生中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时能倏然想起那本书的内容并由此获得慰籍。”这就是芭娜娜的文学理想,是吉本隆明所说的“不同的小说概念”,也是芭娜娜取舍文学素材的依据和标准。为此,她选择了普遍性,摒弃了特殊性,她描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排除了历史人物的叱咤风云或耀眼明星的妮紫嫣红。她曾说自己全部的兴趣就在于普通的事物:“在平凡得无法区别的一天,一如既往地来到街上,普通的人们在做些什么”。芭娜娜的这种文学观直接带来了她作品的一大特色—“通俗性”。她本人对“通俗性”的解释是:普通的人能够阅读并理解。为此她在写作时尽量避免出现阻滞读者思维的情况,她希望即使是与书无缘的人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也能够顺畅无阻。芭娜娜在创作过程中首先把自己置换为一个读者,她总在不停地揣摩读者希望通过阅读获得些什么,同时想象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这与村上春树“尽可能让作者与读者处于并列位置”的原则不谋而合。芭娜娜创作时的价值判断来源于读者的好恶,而非专家学者的评论,或编辑人员的意向、文坛同人的希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吉本隆明说她是“读者专家”。芭娜娜为实现通俗性而采取的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渲染情绪。情绪是时间、地点、情节、人物、环境等小说诸要素当中最不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之一,却是芭娜娜最为重视的一项。她认为,“世界各国的人能够共同理解的东西不是语言,而是类似于情绪的东西”,比如“在这样的天气里做了这样的事有了这样的心情,在这种心情之下走过这样的地方于是情况变成了这样等等”。因此,她总是着意去捕捉人在某个特定瞬间的极其微妙的心理感觉。她的作品往往于不经意间、在读者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触动他们内心深处最为脆弱和柔软的部分。当然并非通篇都遍布着与读者情绪的接合点,不同的读者总是对不同作品的不同细节有着特殊的感触,在阅读进行到某一特殊位置时才能感受那种因共振而形成的心灵冲击、体味因理解而带来的悲喜交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芭娜娜认为小说是“一对一”的艺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是“一对一”的关系,小说营造的情绪渗透于读者内心,读者也由此深入到作品内部。芭娜娜文学的通俗性还反映在叙述语言上。她的作品中,第一主角几乎都是20到30岁的年轻女性,同时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仿佛是女主人公在向读者娓娓倾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语言风格简洁平实,带有显著的口语体色彩。日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非常大,书面语整伤、规范、明确,口语简短、随意、暖昧。芭娜娜作品中频繁出现大段的人物对话,此外还有大量的心理独白。这部分语言几乎没有经过文学的润色和修饰,如果诉诸声音简直就是日常生活的录音片段。其中还包含了许多日本现代生活中、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使用的理语、流行词汇以及刚刚出现的外来语,等等。即使是叙述语言也都简单明了,以短句居多,没有日语正式文体中常见的那种烦琐冗长的敬语,从而摆脱了敬语所特有的生硬疏远的感觉,因此非常接近生活的原样。另外,芭娜娜多使用浅显易懂的假名词汇,而极少那些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所喜用的艰深的汉字词汇。就连数字也大都是阿拉伯数字而不是汉字。日语是竖行排列,一旦出现阿拉伯数字就不得不改变阅读方向,所以一般来讲都采用汉字表示。但芭娜娜却乐于使用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的、一目了然的阿拉伯数字。综观全篇,汉字所占比例很小。由于假名在纸面上占用空间较之汉字要大上几倍,一个汉字通常可以对应数个假名,而大量存在的对话又需要不断换行,所以也有一些持否定意见的评论者批评芭娜娜的作品是“注水小说”,缺乏内容,借助分段留白等手段来拉长篇幅。尽管芭娜娜的文学语言本身非常朴素,然而营造出来的氛围却细腻玄妙,极富感性,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超现实吉本芭娜娜的很多小说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只是简短的话语连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或是与人谈天讲述自己的故事一样,有种自然亲切的感觉使得读者的情绪随着她悠缓的语气而起伏。小说中简单的模式中追诉往事这一倒序方式,像是再跟读者对话,以开始的结局引起读者的想象,为探清缘由而有接着看下去的欲望,又起到了拉开读者与文本距离的作用,适时地提醒作者这是别人的故事。除了倒叙这一手法,超现实描写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小说的主人公沉陷在无边的黑暗中时,超现实现象总是以梦境或超能力者显现能力的形式进入她的生活,从而形成了亦真亦幻、真真假假、神秘无解的艺术境界。吉本小说的巨大感染力量是她的感性的描写显现的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悲剧力量。但是她的目的并不是无限制地使读者哀伤下去,最终的目的还是让读者认清现状从黑暗中走出来,让读者振奋起来,努力改造人生。吉本芭娜娜为了达到她期望的效果,巧妙地植入了超现实的描写,帮助读者从哀伤的故事中摆脱出来,仿佛芭娜娜在强化一种生活观念,是运用艺术描写的方式在强化。芭娜娜在小说中添加超现实元素,造成了一定的间离的效果,让读者沉浸于小说人物的悲伤忧愁之中的同时,可以适时地审视自我、调节自我,不忘领会吉本芭娜娜这样写的目的和意义—调整自我从悲伤中走出来,回归现实,正视现实。
更多吉本芭娜娜资料>>

 对日常性死亡事件的现代性书写是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真实的日常性死亡主题在她的笔下反复出现,形成了吉本小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死亡”是吉本切入现实、品评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她契入故事的缘起。在她的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她的这个“独特视角”在审视故事的进展。例如在《厨房》中,“祖母死了”,平淡的一句话引出一段孤独、曲折的城市故事,由此樱井失去了所有的血亲,失去了安身之所,走人了一个无任何血缘关系、陌生的家庭。
对日常性死亡事件的现代性书写是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真实的日常性死亡主题在她的笔下反复出现,形成了吉本小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可以说,“死亡”是吉本切入现实、品评人生的一个独特视角,也是她契入故事的缘起。在她的每一篇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她的这个“独特视角”在审视故事的进展。例如在《厨房》中,“祖母死了”,平淡的一句话引出一段孤独、曲折的城市故事,由此樱井失去了所有的血亲,失去了安身之所,走人了一个无任何血缘关系、陌生的家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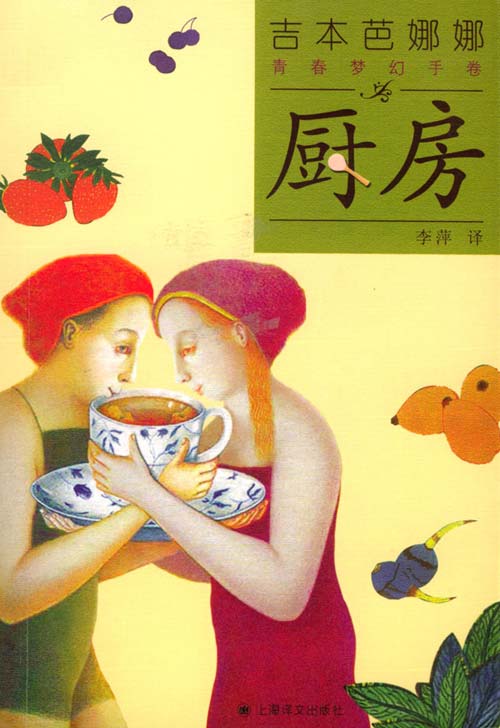 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与死的非对立性。死蕴含着生,生也包含着死。死是人生的极限,个体的毁灭,死的份量是无法估量的,它留给读者的应该是无尽的痛苦。然而,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是,吉本小说中的死亡留给读者的往往不是悲哀、沉重的感受,而是通过死亡事件描写处于极限中的人际关系,无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中产生的类似家族成员般的温情表现;通过“死”的体验,建构一种深层次的真实的人性关怀;通过“死亡”这一极限的设定,达到一种丧失语言的极限状态,从而与死相关联的主人公们,在处于极限、经历苦难的心路历程之后,感觉、视觉变得多层次化,从而进一步打破惯常的价值观,体味丰富的感性,建构起新的心理价值。
吉本芭娜娜小说死亡主题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与死的非对立性。死蕴含着生,生也包含着死。死是人生的极限,个体的毁灭,死的份量是无法估量的,它留给读者的应该是无尽的痛苦。然而,不同于以往文学作品的是,吉本小说中的死亡留给读者的往往不是悲哀、沉重的感受,而是通过死亡事件描写处于极限中的人际关系,无血缘的家庭共同体中产生的类似家族成员般的温情表现;通过“死”的体验,建构一种深层次的真实的人性关怀;通过“死亡”这一极限的设定,达到一种丧失语言的极限状态,从而与死相关联的主人公们,在处于极限、经历苦难的心路历程之后,感觉、视觉变得多层次化,从而进一步打破惯常的价值观,体味丰富的感性,建构起新的心理价值。







































